文章来源:Mountains群玉山(id:Mountains_0)作者:群玉山研究院
原文链接:刘德寰八问马晓波:回答关于创作的一切
/ 编者按:
一位社会学出身的传播学教授,与一个注重社会关怀的商业内容创作者,针对兼具「商业性」与「公共性」的文本创作,他们的思考和对话能够给我们什么启发呢?
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、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导刘德寰老师,与群玉山品牌咨询机构马晓波先生,在2023年的这场对话,提供了许多问题破局的线索。
群玉山研究院整理了他们的这场对话,供各位参考。

刘德寰:
你从小在宁波长大?
马晓波:
在宁波慈溪长大,大学毕业以后先在北京工作。
刘德寰:
在慈溪长大是什么感觉?
马晓波:
慈溪跟余姚和绍兴的关联,反而比宁波要强。余姚有四大乡贤——严子陵、王阳明、朱舜水、黄宗羲,绍兴又有鲁迅,整体文化氛围不错。那时候乡镇企业家、个体工商户也多,大家都爱捞钱。
读高中时,我的很多同学已经有BB机了,流行抽红塔山,穿那种温州生产的假洋鬼子金盾衬衫,用特别浮夸的钻石扣,从小几乎没过过啥苦日子。
我父亲在文管会搞瓷器考古、保护、研究相关的工作,母亲做中学老师,身边同学的家长要么是国营厂的,要么是医院、教师体系内的,生活整体向好。因为消费水平高,像中华烟、酒鬼酒、茅台酒,慈溪市一个县级代理商,能拿到省级代理的权限。
小时候还有很多文化活动,民乐、写作、书法,各种各样的比赛、补习班。
我后来急于离开老家,特别是读了大学后,见识过外面的世界,就觉得这块天空实在太小了。
刘德寰:
那时你对未来的想法是什么?
马晓波:
我文字天分还不错,很小就能写一些简单的格律诗、微小说之类的。读高中时,很明确想做广告,高考就想报厦大的广告系。
但父亲不同意,他觉得做广告特别忽悠。后来他找了一个迂回的方式跟我说,你的性格非常跳脱,缺乏逻辑性,相信做广告是需要逻辑的,所以大学应该去补一补天性不足的东西。
他建议我去学法律,后来我才知道他也是随口一说。我被他忽悠了,读到后面非常后悔,身体和精神都在说,这个东西我一点都不喜欢,而且学的是国际经济法,太过痛苦,基本上大三我就放弃了。大一大二还在法院实习,大三大四就开始去广告公司做兼职文案。
那时还没有网络媒体,软文都发布在报纸上。大三大四很多零用钱是靠写软文挣的,可以说我很早就从事广告业。
刘德寰:
父亲让你去读法律,你很难受,但现在反过来看,有没有优点?
马晓波:
肯定有。广告不是一个纯创造性的工作,创造是最后一步,前期需要分析、归纳、提炼,跟法律有一定的相似度。比如同样是一个案子,你要知道这个案子的核心冲突到底在哪里,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什么。
学法律,特别是经济法,一个案子不管多复杂,总有核心冲突、核心诉求、核心主张。这些核心问题被解决之后,其他都是小问题。
怎么锚定核心问题,怎么收集所有的证据,哪些是从实体法条里去找,哪些是从案例里去找,这些都很相似。但最终结果大不一样,广告需要创造性地解决问题,法律更偏向理性地工作。

刘德寰:
困在法律里,你的天性就发挥不了。
马晓波:
我是一个不喜欢在细节的迷宫里面打转的人。文字的风格跟人的性格有很大关系。有几个行业里的朋友文笔极其细腻。他们喜欢用显微镜看细微美好的东西,我喜欢坐着滑翔伞,看一下山川走势、河流走向,一讲就往大里讲。
客户一跟我讲到很多产品细节,我就会本能地厌倦,不想去看这些细节,甚至会离它很远。就连客户邀请我去看厂房、生产线,我一般也不去。一双鞋也好,一台手机也好,我会产生一些浪漫的联想,但是你现在直接把它放在解剖台上看这些「尸体」时,我不会有任何感性的想法。
刘德寰:
这恰恰说到了非常根上的一件事儿。品牌实际上并不是我们看到的公司的样子、厂房的设备,而是我们脑子里面模模糊糊的东西。作为创意人,了解越多的细节,越无法创意,因为你被限制死了,被限制在那些具体的视野当中。品牌是什么?广告人对一个品牌的感觉,越是没去过那地儿,感觉越跟大众一致。
马晓波:
当时我也跟很多企业家讲,让我离你们远一点,远一点我会看得更清楚。只要跳进去,就是循着你们的思维,看着你们的东西,很难有新的想法。
还有个特别明显的感受,希望大家跳出商业和经济领域,多从社会学角度去看看,有时反而会更明确一点。
比如我们借用了米勒的「拾穗者」概念。很多消费品牌就跟「拾穗者」一样,市场的整片麦田已经被收割得差不多了,有极大红利和增长空间的品类很少,只能做一些小品类,饿也饿不死,但营养是不够的。
在这种情况下,你能不能把不同的麦穗捡起来?不同的麦穗代表不同的小问题、小需求,你最终找到超越传统品类的方法,把这些小需求拼起来。就像百货公司的服装货架、化妆品货架、饮料货架,原本是不连通的,但借助某个新场景下的新概念,把不同的货架打通。
比如蕉下既有服装,又有生活百货,有一切能让你在户外玩得开心的东西。「轻量化户外」的使命不是为了让你变成一个英雄,而是变成一个更亲切的普通人、更好的爸爸、更好的老公、更好的朋友。我们相信在户外,人跟人之间的关联会更亲密。所以蕉下做清酒、防蚊液都很合理,只不过防蚊液是一颗小胶囊,有很强的连接性和分享性。
这样它就把以往户外场景里面不相干的品类聚到一起,最终组成一个更大的解决方案,解决普通人去户外的一站式购物需求。原本做物理防晒,两三百亿就见顶了,而且只能做夏季,但「轻量化户外」可以做四个季节的生意。
所谓赛道重组这个概念,就是把小的麦穗捡起来,组成更大的麦穗。

刘德寰:
我有时会想起「百年润发」,这是一个很好的广告,故事讲的是知青返城,这波人最大的特点是下岗职工比较多。结果广告火了后,人们发现产品定价高于宝洁,完全是好好做了广告,却把自己作死了。
马晓波:
我们经常讲,好广告会让一个烂品牌死得更快。因为好的广告会提升消费者对品牌的预期,如果品牌自己接不住的话,心理落差会变得非常大。
刘德寰:
为什么要拿最不起眼的一款商品,打开「轻量级户外」这个口子?听说那款鞋最初没有「惊蛰」二字,是因为广告后加上去的。
马晓波:
它本身防晒的认知太强了,超过80%。当时我们做了300人左右的调研,在路上街访,逮住一个人就问,你知不知道蕉下?蕉下是干什么的?答案都是防晒。所以挑第一波产品的策略是,一定要找一个离它原来产品最远的东西,这样才能把认知拓宽。
当然这产品还得是一个户外必需品,最后定了鞋子。又为了产品名、节气名、创意名合一,达成最强的统一性,就挑了一批鞋做成限量版,重新设计字体,写上惊蛰。
当时对标的是什么呢?我们发现一个市场空白——大牌的低端线。很多人去徒步、春游,很少买价格超过1500元的专业户外鞋,绝大部分穿的是阿迪达斯、耐克三四百块的鞋,这批鞋不具备户外功能。
刘德寰:
先找来300人做街访,是做品牌画像?
马晓波:
做认知调查。我们做品牌升级首先要明确「我的A点在哪里」,之后才知道B点怎么走。
他们一直说自己是做物理防晒的。按照我们的理解,消费者心里不会有防晒这么一个品类,所以就做了次调查,结果发现防晒的认知确实很强。
刘德寰:
「轻量化户外」这个定位怎么得出来的?
马晓波:
最初我们认为需要打造一个新的认知,当时拿了三个词去测试:城市户外、轻户外、精致户外。
整个调研下来,城市户外被杀了,消费者认为这个词没有向往感,这是很致命的事情。轻户外也不行,相当于专业户外的低配版,没有价值感。
剩下精致户外,最初大家已经达成共识了,比起同价位其他品牌,蕉下整个设计确实更具时髦感,另外精致是一种心理需求,大部分人不愿意跑去户外受苦,最好能吃好喝好玩好。
但是我一直觉得这件事情还是不大对。一是精致户外太聚焦在设计跟外观上面,缺乏技术感。我不是要去跟专业户外比科技、比创新力,但一个面向未来的赛道是不能丢掉专业化表达的。二是精致这个词在公众语境中有点异化,被当做一个贬义词在用。
后来我说,我们可能从户外领域找不到这个定义,要求团队去研究一下不同的科技领域有什么趋势性的概念。它得符合几个标准:第一,有代际化优势;第二,可能是很多科技领域发展的共同趋势;第三,听上去简单明确,易于产生正面的联想。
有一天团队跟我说,汽车底盘经历过一个轻量化的过程。我说轻量化这个词好,手机、电脑、甚至很多建筑材料都经历过轻量化过程。
再往下研究发现,轻量化这个词跟仿生学是高度捆绑的——存活到现在的物种,不管是植物还是昆虫,它的身体都是能效比最高的结构,在单位面积里面释放最大能量,否则不足以在自然界生存,像恐龙这种非轻量化的东西就被干掉了。不同领域做轻量化的过程,都把仿生学作为一个主要的研究路径,它也是技术演进的一个重要路线。
同时「轻量化户外」可以跟蕉下以往十年的发展历史串联到一起。品牌升级不能抛弃原来的历史,否则消费者是不相信的。
这些东西全部拼起来之后,成了「轻量化户外」,它符合户外发展趋势,同时又代表一种生活方式。生活方式最终处理的是人跟时间的关系——我把时间放到哪里,就意味着我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样的。「轻量化户外」面临非常庞大的群体,差不多4亿中产。

刘德寰:
怎么塑造品牌跟消费者之间的亲密关系?
马晓波:
通常来说,品牌总想展示自己是多么了解消费者,他们会深入挖掘消费者的痛点和爽点,通过所谓的「消费者洞察」,深入到细节中去。
我甚至有段时间不想讲洞察这个词。洞察的问题是心态上在迎合消费者,就像追女孩子一样。当然它是一种重要的作业方式,但如果成为唯一作业方式的话,视角永远受限。
后来我们自己总结,还有什么样的方法,可以更简单粗暴地讲出新故事?
第一种方法是魅力最大化。任何一种性格、气质、审美特质被发挥到极致时,会拥有很强的感染力。如果你能把一个品牌做得严肃到极致,也挺可爱,人们会觉得有趣。
第二种方法是二元对立。这是我们最常用的方法之一,它不是在人群上切割,而是在心智上区分。比如《后浪》一刀切下去,把人群分为前浪和后浪,就看你自己怎么归类。这种方法一下子把所有对手做了一次反向的定位,给自己切出一个更大的增长空间。
如果把这两种方法进行一定程度的融合,就是第三种方法,为品牌找到一个共同的「敌人」。当然,这个敌人不是具体的某个人或事,而是人性中的某些阴暗面或弱点,是那些无法彻底消灭的东西。这样一来,品牌与消费者之间就形成一种长久的联盟,因为一旦敌人消失了,这种联结也就不复存在了。
比如Nike的「Just Do It」对抗的是懒惰;Johnnie Walker的「Keep Walking」对抗的是懦弱;Mercedes-Benz的「The Best or Nothing」对抗的是平庸;Apple的「Think Different」对抗的是随波逐流;方太的「因爱伟大」,对抗的是冷漠。
这些品牌都在挑战人性的某个方面,传递一种价值观,也表达品牌在人格上的特质。这个思路已经成为我们的一个小秘诀,先为品牌标注一个人性对手,这种对抗给我们的创意带来感染力。
再比如半分一对抗的是狭隘,它不断鼓励女性追求更宽广和未知的精神世界——不管走多远,你都只走了一半。后来听创始人讲,这种理念和价值观促进了一笔产业投资的敲定。
刘德寰:
品牌理念看上去是最虚幻的东西,但实际上什么都没有理念重要。如果一以贯之地做下去,结果完全不一样。

刘德寰:
过去这么多年,最让你兴奋的案例、最有挫败感或者最后悔的案例是什么?
马晓波:
最兴奋的还是《后浪》。创作离不开创作者自己的认知,因为你不可能去写你不认同的东西。我最喜欢的三个案子,一个是Timberland《踢不烂》,一个是《后浪》,还有一个是快手的《可爱中国》,这是我当时最喜欢也最认同的三个东西。
《后浪》是2020年做的,是我2015年到2020年,整个五年中一些点点滴滴所思所想的合成,总体性的一次输出。
当时抛弃了非常多的写作原则,完全是一次痛快的、没有限制的输出。我坚决认为,必须把我想讲的东西全部讲出来,所以那次是最痛快的一次,不管别人认不认同,自己先认同了再说。
至于有遗憾的案子,其实每个案子都有遗憾,最后悔的应该是蕉下的第二部曲,防晒衣的那条爱情微电影《所有的太阳》。这是我第一次在客户面前退缩。
我当时认为,第一条片子做的是鞋子,第二条应该走到起点,在户外场景重新讲述一次防晒衣的价值。而且我不想做价值观的表达,还是要做强产品表述。怎么包装呢?我们选了一款爆晒级防晒衣,产品力本身是支持的,它可能不是最轻的一件防晒衣,但一定是防晒力最强的,扛得住99.99%紫外线。
但品牌那次受「惊蛰令」影响比较大,他们认为,像「天下无路不可走」这样的价值观是非常有效的东西,而且他们觉得产品做得很好,也保持了市场的领先地位,这次更应该赋予防晒服一个产品价值观。
我当时是反对的。防晒衣是基本盘,基本盘竞争激烈时,反而不应该去讲价值观。大家都在做防晒衣,蕉下作为防晒衣最大品牌,应该把产品的价值再往上塑造一层。
但客户比较坚持,我就没坚持。我说那行,价值观可以有,就是「我们穿上防晒衣,不是因为害怕太阳,而是为了拥抱太阳」,展现一种更热烈拥抱世界的姿态。
这个价值观也很好,在业内很受欢迎,上了各种榜单,但是无法促成销量增长。
后来跟客户复盘,我觉得自己要承担最大的责任,在策略层面没有坚持。也不是说一定能严谨准确地预判一件事情,而是经验告诉我,那个时间点应该做产品营销,而不是品牌营销。这应该是我好几年来最后悔的一次。
当时三部曲的目标是把「轻量化户外」的定义撑起来,这三波要非常强力,全部打透才行。它的连贯性要非常强,一步一步把势能积蓄起来。
刘德寰:
你谈到的实际上是品牌跟产品广告的组合问题,组合中有战略部分和战术部分。在战略上,一定是以品牌理念和价值观为先导;在战术上,要以产品推广为核心。两个东西合成相配才是标准做法。
品牌认为第一步价值观输出成功后还要再打一次价值观,实际上这恰恰是一个冲淡主题的过程,再好的东西你说了两个,都是冲淡主题。
品牌的逻辑是一以贯之。产品的逻辑是不断推陈出新,逐步迭代。
马晓波:
是的,这个组合最终是为了说服用户认同这次定位升级。
我的最初设想是:第一步,我们走到最远的边界,先给你看双鞋子,你不要以为我只会做防晒,我们连鞋子都做。而鞋子是户外必需品,是很重要的东西;第二步,我走回原点,把防晒衣做一次技术升级和体验升级,可以应对多元的天气状况;第三步,就开始讲「轻量化户外」策略,有伞、有靴子、有墨镜、有防晒衣、有冲锋衣……
三部曲不是一次性把三个案子全部想清楚,一般只会有大概的框架思路。第一部讲完后,根据市场反馈来看第二部大概怎么做。第二部结束后,再看一看前两部的反馈,再决定最后一个案子的内容和基调。每次行动都根据前一步的结果来决定下一步,这样的动态调整本身是策略的一部分。
当时《后浪》第一部注重的是煽动性——煽动年轻人的进取心,做完之后市场反馈非常激烈,我们想稍微反向抚慰一下;到第二部,就变成要正视年轻人面临的困境,但从市场增量来说,要抓住那会儿的毕业生,所以做了《入海》;到第三部《喜相逢》,又变成我们都是爱学习的人。
我们打了三次求同标签——不管是曾经的还是现在的,我们都是后浪,我们都是毕业生,我们都是爱学习的人。

刘德寰:
刚刚聊到品牌与消费者的亲密关系,你怎么理解创作者和观众的关系?
马晓波:
我觉得,创作者是一个分享者的角色。松下幸之助讲,销售的最高境界是把你喜欢的东西分享给别人。你喜欢一支口红,你要把它分享给消费者,带着真实的体验、真实的感动、真实的表达,这种姿态是最平等也是最亲密的。
我后来借用鲁迅的半句话来理解广告这件事——把我们相信和感动的东西,分享给无穷的远方和无数的人。
所以我们做广告时,首先会弄清楚品牌的诉求,到底想争取什么样的人群,想卖什么样的东西,包括有形的商品和无形的价值观,但更深层次上,我们还有另外一个身份:创作者。
创作者讲究寻找到真实的感动,在各种各样的故事中,找到自己真正感动的东西,同时坚信自己是一个常人,这是我们内部很重要的一个价值观——不要把自己当作一个小众、另类、独特的人,而是一个常人,你所感动的,绝大部分人也会感动,你为之悲伤落泪的,绝大部分人也会哭。最终怎么把自己的感动变成绝大部分人的感动,这才是一个专业问题。
在此之前,想象你面前坐着一个朋友,他愿意给你5分钟、10分钟,听你讲一个故事,这时你会分享什么给他们听?创作更像朋友间的故事分享,是一种分享关系。
我们分享的一定是自己喜欢的东西,而不是我发现这个人有点钱,就揣摩跟他说什么,他才会把钱给我,那个姿态很低级。一个脱口秀演员,一个舞蹈演员,或者一个流浪歌手,站在街头弹唱一首好听的歌,大家都可以大大方方在胸口放一个二维码收钱,只要分享的是自己喜欢的东西,也很浪漫对不对?
刘德寰:
现在一说什么东西,都喜欢用营销的话术,这个痛点,那个洞察。这些词太功利了。很多人说我是做企业的,当然要功利,要挣钱,实际上他们错把人当成了消费者。
如果营销人只盯着人的钱包,那就是不把消费者当人,正因此大家对于营销人是反感的。但如果一个品牌的传达,不是基于这种鸡贼式的营销,而是基于对人性正向的传达,这种感染力本身不是营销,却好于营销。
关键在于,人还是人,消费仅仅是人的行为,不能把人简化成消费者。
马晓波:
刘老师说得特别好,如果把人当成消费者,所有心思都会局限在消费者动机上。
营销专家说洞察人性的潜台词是洞察人性的弱点,实质是利用人性的弱点来挣钱。人性也有积极美好的一面,我们能不能放大正向的那一面,比如追求进取心、勇敢、无私、善良、诚信、浪漫的一面。
有一次,我重新翻阅 Timberland 2018年的广告,它激励过不少人,我就顺手在小红书上分享了穿 Timberland 大黄靴的照片,配文提及了那几句广告词。
有个女孩在小红书上联系到我,我们并不认识。她说:「马老师,我想买一双您在视频中穿的那款鞋,希望能附上那段旁白,因为那句话改变了我的人生。」
我好奇地询问详情,原来她毕业时面临选择。一边是留在大城市考研追梦,一边是回家乡过安逸生活。犹豫之际,无意间看到我们的广告,一句台词触动了她,让她坚定了继续在大城市追梦的决心。她提起在北京的奋斗,虽然辛苦,但很确信这是自己热爱的路。
我很感动,送了她一双大黄靴,只让她象征性给一块钱,因为送鞋不收钱是不吉利的。
那是做广告最快乐的时刻,你在一个人的关键节点影响过她的选择。
我们内部常讲,如果广告在达成商业诉求之后,还能够影响到人,小小地改变人的一些想法,给人一份感动或启发,所有努力就有了价值。这也是我们用来激励自己的东西。
刘德寰:
而且这件事实际上是自然的,消费是人性的一部分。当你跟人性美好一面接近的时候,做出有感染力的广告也好,公关活动也好,带来的价值是超过商业利益的,而且商业利益绝不会少。
战术上,该赚钱必须要赚,战略上一定有更高层面的东西。
马晓波:
一方面,我们已经看到消费者在成长,他们在努力变成更好的人;另一方面,创作机构也好,品牌也好,有能力在赚钱的同时输出更好的价值观,为什么不做呢?只想赚钱会让这个行业变得没有魅力,没有感召力。就像高考填志愿时,我父亲觉得做广告是忽悠人。
但我最自豪的是什么?我做的一些广告,我爸是会转发的,他是一个有心理洁癖的人,他会转发意味着他觉得这是他认同的东西。
刘德寰:
把这种理念贯穿在作品中,这是一个有理想的广告人的基本逻辑。
马晓波:
就像很多流量小鲜肉,你已经取得一定的成功了,为什么不能探索一下演技,成为一个演员呢?说白了就是别老想着挣钱,把自己当成一个商品。

刘德寰:
你怎么理解公共文本?
马晓波:
公共文本最基本的设想,是以某个社会横截面或者社会议题为核心来叙事,给出自己的立场和观点;它有着可被二次解读、二创的特性,就像刘老师说的,它是开放性的文本;同时它得具备可留存的价值。
我自认为最好的两次叙事,一次是《后浪》,一次是Timberland,但Timberland明显缺乏公共性,更多还是自我态度的表达,并不是在阐述我对一个大议题的看法。
刘德寰:
实际上自我表达是极其重要的人生追求,个人价值的表达是每个人自我实现的最高层级。
我认为还是要看做品牌的同时是不是在构建社会价值。任何能够体现人性积极面,具有正向意义的表达都可以视为公共文本。
它不一定是一系列逻辑性的表达,更多是一种感染。而感染本身所带来的社会冲击力,会远远强过一篇论文。一个文本只要让很多人走心了,它就是一种公共文本。
马晓波:
感染力优于说服力。
刘德寰:
感染是一种情绪的传递,也是能够塑造人的根本的东西。
马晓波:
刘老师提出的「飘一代」这个词,对我造成比较大的冲击。
起初,我将它视为城市化进程中新移民的代名词,但现在看来,这个概念其实更加宽泛。在全球局势和中国进入一个平缓甚至下行期的当下,「飘一代」已不再局限于特定群体,而是涵盖了我们这代人。
我们进入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漂泊时代,不知道世界走向哪里。特别是对于我们这些70后,曾经走过坚固平稳的陆地,尽管有上坡也有下坡,但大地岿然不动。现在突然感觉大陆板块被打碎,你一脚踏进海水之后,真不知道会往哪里漂流。
「飘一代」这个词能激发群体共鸣,也反映了社会现状,在我看来就是一种公共文本。
刘德寰:
在实际运作中,文案作为传播工具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。你是怎么看待文案的?
马晓波:
第一阶段,我对文案的看法是,它不改变事实,只改变人们对事实的看法。这是我对于麦肯那句「巧传真实,善诠涵义」的理解。
比如,西瓜就是西瓜,这是事实。但如果我告诉你,西瓜的卖家是一位70多岁的老太太,孩子在国外,没人照顾,她唯一的朋友就是这些西瓜,她像照顾孩子一样细心照料。这样就通过讲故事的方法改变了你对事实的看法。
或者场景法,在最炎热的夏天,一个女孩坐在瀑布边,梳着麻花辫,不是小心翼翼地吃,而是一下把这个瓜砸到石头上,瓜瓤哗一下散开,她狼吞虎咽地吃瓜,在带有青春气息的叙事里面,这个瓜被塑造出一种热烈的爽感,也是在改变你对事实的看法。
早期我们大量运用这些原则,但后来发现文案不仅可以卖货,还可以承载更高的价值。像Timberland和《后浪》都是这种方式,在商品之上塑造它的价值观——真诚地相信自己的所思所想,坚定地把它分享给所有人。
最后,我觉得这无关专业,而是个人追求,文案应该有技术含量。比如以言建寺,文案能像诗歌一样有强大的感染力,有种宗教感在里面。
一个建筑师朋友有天兴高采烈地说自己在做一些环保型建筑,我当时听了很感动,大部分广告文案很泡沫化,大家听了爽一把就结束,没有建设性,不真正带来精神的力量。
刘德寰:
刚才聊到,你的家乡出了非常多的文人墨客,这些人对你的文案风格有影响吗?
马晓波:
肯定有的。我爸本身也喜欢古文、书法。小时候,他带我散步的路上就会教我古诗词。我越长大越觉得诗词魅力无穷,心烦意乱时朗诵一下雨霖铃啊、念奴娇啊,是很好的享受。
在文案技巧上面也有一定的影响。国外有很多精彩的长文案,写得漂亮,有冲击力,但它没有中文本身的节奏感、韵律感。后来写《可爱中国》和《后浪》时就下意识想尝试一下中文语感的长文案,它确实更像汉赋的感觉。
我喜欢苏东坡、柳永,他们有豪迈的一面,写的东西气象很大,有时柔中带刚,有时刚中带柔,你能从里面学到情绪表达的层次感。比如柳永写「千里烟波,暮霭沉沉楚天阔」,后面又说「今宵酒醒何处?杨柳岸,晓风残月」,开场辽阔宏大,收尾轻轻落地,特别美。
我们的创作姿势应该更自由一点,大家很多时候太小看消费者了。在商业广告里面,我做过一次非常大胆的尝试。以前我们被训练说广告词一定要写得每个人都能懂,这没错。但有一次我偏偏想,能不能做一次绝大部分人看不懂的东西,给产品写一首宋词?那是很成功的一次尝试。
那年中秋,我们给方太的油烟机、洗碗机、蒸箱各写了一首宋词,做了一波整合营销,投东方台、北京台,三个30秒连播,还投了很多机场、地铁站。我跟同事们说,敞开玩好了,没关系的,要相信消费者是看得懂的。果然,那次的市场反馈甚至销售反馈都非常好。

刘德寰:
你们这种对社会的理解和观照,非常像60年代七喜的广告,有导向性,但这种导向与政治无关,而与整个社会价值体系的深刻变迁有关。
60年代美国经历冷战、越战,包括马丁·路德·金当时也在领导黑人民权运动。这一系列的社会动荡,促使人们形成了以怀疑为核心的思想,不愿说YES,而是NO。
基于此,七喜打出了一个非常强悍的广告:「非可乐」。当时排名第一的饮料是可乐,这个广告就与社会价值体系完全对接,迅速获得了社会的认同。
到了80年代,整个社会批判的逻辑还保留着,但是人们的怀疑性减弱,开始关注健康,七喜又提出「无咖啡因」概念,既保持了NO的精神,又跟健康思潮崛起相关。
你们现在做的事情,与七喜的做法非常像,本质上是理解了时代和社会的深刻变迁之后,把这种东西以一种正向的、带有很强引导性的方式,给推出来。
马晓波:
这其中的关键是找到民众共识,或者说共同价值观。
这个共识不是那种自上而下,强加于人的价值观。而是由大众共同参与创造的价值观。只有这样才能形成真正的共识基础。
当然,肯定不能脱离传统价值观。我们不能凭空捏造出一套全新的现代价值观,那是不可能的,它肯定来自中国丰富的传统价值观体系。
刘德寰:
谈这个话题,我们得看中国社会这几十年的变迁。「快」成了关键词,随之而来的,是人们遗忘的速度也变快,大家不愿意花时间去沉淀和积累。另外,独生子女政策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,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一代人的成长和价值观的形成。
这代年轻人,身边总围着大人,一定程度上缺少了自主性。这种情况导致长大后的自我中心倾向,加上忙碌和压力,信任感的建立变得困难。这样一来,无意间塑造了一个奇特的社会现象——同龄人之间互相碰撞,摸索新的价值观。但这些新观念没有经历历史检验,就快速迭代,旧的观念被轻易抛弃,导致了80后这个群体出现价值观的迷茫。
而世代之间的这种差异,是一个过程导致的。过程导致的差别要比价值导致的差别,改变起来难得多。在这种情况下,没有人愿意被传达,在情感当中去体会才是最好的。
马晓波:
我在观察B站的时候,倒是发现了一个正面例子。B站的社区氛围,或者说它所代表的部分年轻人的共识,是崇拜有真本事的老人,听前辈的话。
B站有一次为五四青年节做策划,邀请了莫言这样的老前辈,宣传「不要被大风刮倒」精神。这种策略相当巧妙。
莫言这些老前辈,既是人生的过来人,又是知识的传授者,就有很高的说服力。我当时还在我们群玉山的同好群里,针对这个现象写了一篇文章,大致意思是前辈如同我们在时代洪流中的灯塔、锚点,看到他们,能帮助我们定位自我。结果引发了很多人共鸣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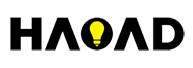


 HAO-AD
HAO-AD





